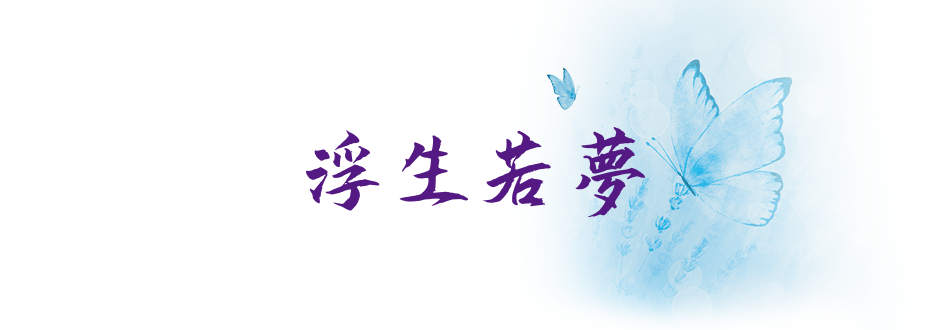
有一天,莊子做了一個夢,夢見自己是一隻蝴蝶,翩翩飛舞,快活得很。一覺醒來,才驚覺自己還是那個叫莊周的人。可是,剛才的夢境太逼真了,莊子不禁疑惑:自己究竟是莊周,化蝶只是一場夢;抑或其實是蝴蝶,此刻在夢中化身為莊周?
一夢千年,那隻撲朔迷離的蝴蝶,從此輕輕扇動玄妙的翅膀,觸動歷代文人墨客的心弦,造就無數錦句華章。
“鹿疑鄭相終難辨,蝶化莊生詎可知。假使如今不是夢,能長於夢幾多時。”這是白居易仕途受挫後,對理想幻滅的愁懷悵惘。
“莊生曉夢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鵑。”這是李商隱追憶舊情的纏綿情思。
“蝴蝶夢中家萬里,杜鵑枝上月三更。”這是崔塗對故鄉的眷戀思念。
“枕落夢魂飛蛺蝶,燈殘風雨送芭蕉。”這是黃庭堅對亡妻的緬懷念憶。
“百歲光陰一夢蝶,重回首往事堪嗟。”這是馬致遠對人生百年轉眼成空的無限感慨。
在眾多夢蝶囈語中,能讓莊子開懷大笑,引為知音的,相信莫過於清代文人張潮在《幽夢影》裏的妙論:“莊周夢為蝴蝶,莊周之幸也;蝴蝶夢為莊周,蝴蝶之不幸也。”張潮好友黃九煙讀到此句時,有感而發:“惟莊周乃能夢為蝴蝶,惟蝴蝶乃能夢為莊周耳。若世之擾擾紅塵者,其能有此等夢乎?”
只有像莊子這樣不慕名利、崇尚自由的人,才會做化蝶這樣逍遙自在的夢。在紅塵俗世中打滾的芸芸眾生,夜深入眠,夢到的恐怕多是功名利祿。唐代傳奇《枕中記》中,落魄書生盧生投宿旅店,偶遇道士呂翁。言談間,盧生自歎人生不得意,有志難酬。呂翁便從行囊中取出一瓷枕,對他說:“子枕吾枕,當令子榮適如志。”當時店家剛開始蒸黃粱,盧生接過瓷枕,見兩端有洞,便低頭細看,只見洞越來越大,於是探身而入,驀地回到家中。數月後,盧生娶高門嬌妻,後來子孫滿堂,出將入相,得到夢寐以求的一切,但也曾遭人誣告,鋃鐺入獄,差點引刀自戕。歷盡人生大起大落,嘗盡寵辱、貧富、得失,年逾八十的盧生在家中閉上了眼睛。待他再睜開雙目時,赫然發現自己仍身在旅店,黃粱還未蒸熟。
雖說功業聲名不過是一枕黃粱,甘願在黃粱美夢裏一晌貪歡的大有人在。清初士人陳潢有治水大才,卻屢試不第。偶訪邯鄲呂仙祠,自憐懷才不遇,半生潦倒,題詩曰:“富貴榮華五十秋,縱然一夢也風流。而今落拓邯鄲道,要與先生借枕頭。”河道總督靳輔看到陳潢的題壁詩,欣賞其才,引他為幕客。陳潢治河十年有功,獲授僉事道銜,不料翌年靳輔遭彈劾,陳潢受牽連而被削職,不久病歿京城。陳潢這番境遇,也真如元好問所言:“邯鄲今日題詩者,猶是黃粱夢裏人。”
呂仙祠內的盧生祠楹聯題曰:“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;想到一百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。”上聯盡顯看破世情的灑脫,下聯卻帶點人生苦短的蒼涼。李白在《春夜宴桃李園序》中寫道:“夫天地者,萬物之逆旅;光陰者,百代之過客。而浮生若夢,為歡幾何?”既然繁華易散,韶光易逝,憂時感傷的詩人不約而同選擇了及時行樂:李白與堂弟在桃李園秉燭夜遊,推杯換盞,醉月飛觴;岑參在涼州與好友徹夜歡聚暢飲,高呼“一生大笑能幾回,斗酒相逢須醉倒”;蘇軾在超然臺上勸友人“且將新火試新茶,詩酒趁年華”。
然而,短暫的歡愉終究不能消除心中困惑。物理學家霍金(Stephen Hawking)與網民交流時,有人告訴他莊周夢蝶的故事,問道:“我們怎樣才可知道,自己究竟是活在夢境還是現實中?”他回答:“我們必須鍥而不捨探索關於存在的基本命題,才有機會知道蝴蝶以至宇宙究竟是確然存在,抑或只是夢中之物。”
莊周夢蝶,還是蝶夢莊周?這個問題恐怕永遠沒有答案。又是初春時節,毛蟲破繭而出,羽化成蝶,飛舞於奼紫嫣紅之間。如此良辰美景,賞心樂事,又何必深究是幻是真?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