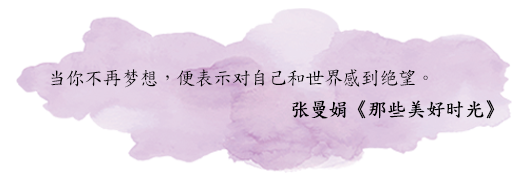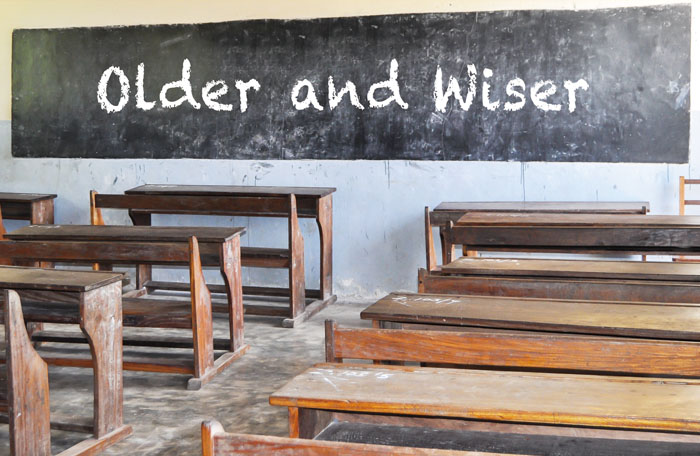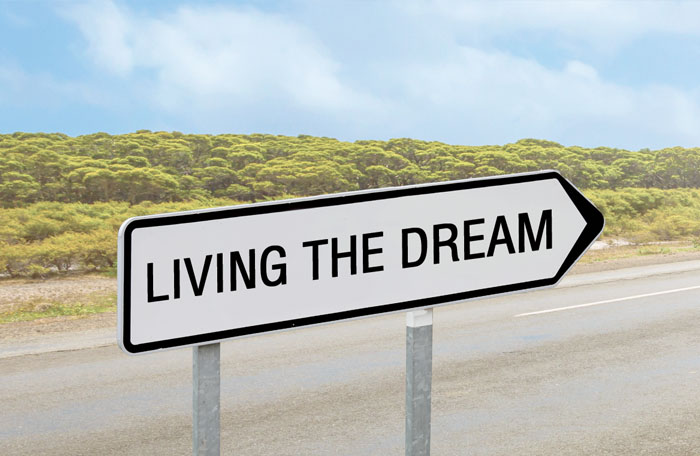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早上十时许,还没到商店开门营业的时候,香港的商场已经人声鼎沸,气氛炽热。这是东京奥运最后一天,港队单车运动员李慧诗正在伊豆单车馆与德国选手轩丝(Emma Hinze)酣战,争夺争先赛铜牌。李慧诗先胜出首场,只要再下一城,便可夺得铜牌。大批市民倚着围栏,盯着大屏幕上的赛事直播,一边挥动打气棒,一边吶喊助威,为“牛下女车神”加油。
从牛头角下村到奥运颁奖台,女车神的封神之路一直崎岖多舛。虽说职业运动员受伤病困扰乃平常事,李慧诗的伤患却来得既早且重。二零零六年,她在昆明集训时摔车受伤,左手舟骨骨折。前后三次手术,折腾近一年,仍未能康复,手腕关节永久失去活动能力。未满二十的小姑娘既被教练质疑当初接受手术的决定,又面临降级压力,身心饱受煎熬。不少人劝她退役,但倔强的她早已视单车为终身伴侣,决不愿半途而废。她扬起笑脸告诉别人:“骑单车是用腿的!”
“无法置我于死地者,必使我更强大。”尼采所言果然极富智慧。断骨的惨痛经历,练就了李慧诗的钢铁意志,使她更能忍痛吃苦。她逐渐学懂克服痛楚,突破身体极限。为弥补手腕不足,她加倍努力,在其他方面下苦功。短距离赛事最讲求腰腹力量,教练要求队员每天做150次仰卧起坐,她自行加操至210次;深蹲训练后,本应好好休息,舒缓刺痛感,她却找人按压痛处,让身体适应更大痛楚,以提升训练量。
经过一番刻苦训练,李慧诗成绩突飞猛进,先在二零一零年广州亚运勇夺金牌,两年后又在伦敦奥运赢得铜牌。她以登山比喻运动员的征途:奋力攀至峰顶后,便要挑战另一高峰,永无休止。登峰临顶不仅需要一双铁腿,更要胸怀一颗斗心。
迈向世界冠军之路荆棘密布,幸有战友沿途伴随。队中与她最亲近的是短途教练普林俊。天冷时,两人在赛道上绕圈训练,普教练骑着电单车为徒儿领骑。李慧诗问他:“那么冷,怎么不戴上手套眼镜挡挡风?”普教练回答:“冷!但戴了就没有速度感了!”比赛前,他鼓励爱徒:“怕什么?比到后面,别人都怕你。”李慧诗灰心流泪时,普教练又安慰她:“骑单车不是为任何人,而是为自己。”二零一六年盛夏,师徒俩整装待发,准备出战里约奥运。当时谁也没想到,那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。
若说李慧诗在伦敦奥运登上顶峰,在里约奥运则可谓陷入低谷。肩负金牌希望的她,在凯林赛与对手意外相撞,无缘决赛,膝盖的伤势也影响了她在争先赛的表现,最终空手而回,四年心血付诸流水。可是,赛场折戟之憾不论如何深切,也比不上永诀之痛。
两个月后,李慧诗赴日本比赛期间,普教练在广州心脏病发去世。翌日,她坚持到场馆训练,一边骑车,一边嚎哭。有选手上前安慰,问她这么伤心,为何仍要勉强训练。答案可在她后来出版的自传《身上的每道伤疤》找到,她在写给亡师的信里细述:
因为只要训练,就会看见您骑着电单车牵引着我;练得累了,就会看见您伸手扶着我;拼命骑车时,就会听到您的吶喊••••••
因为只要训练,就会看见您骑着电单车牵引着我;练得累了,就会看见您伸手扶着我;拼命骑车时,就会听到您的吶喊••••••
身心俱疲的李慧诗在二零一七年毅然放开车把,报读大学写作课程,寻找喘息空间。没有比赛压力,她终于可以肆意熬夜,却发现运动才是她的快乐之泉。她想起普教练“要为自己而努力”的劝勉,领悟到多年来挥洒的汗水与泪水,从来不是为了别人,而是为了自己的“单车梦”。数月后,她重投香港单车代表队,备战东京奥运。
训练日,她在赛道上风驰电掣,争分夺秒;休息天,她在键盘前仔细思量,斟字酌句。日复一日,李慧诗就这样在单车与文字之间穿梭奔驰,直至东京奥运的战鼓响起。
铜牌战来到第二回合,李慧诗骑至最后一圈,从外档压向内档,双腿一提一蹬,加快脚频,车轮疾转如风,后劲刚猛如雷,在最后一个弯位追至与轩丝平排,转入直路后一举超前,率先冲线,成为香港首位两届奥运奖牌得主。她亲笔撰写的自传也在这一年完稿,并于翌年付梓,一圆追寻十多年的写作梦。
多年来,李慧诗视腕上的疤痕为花茎,以血泪与热情浇灌,终于手握奖牌,让梦想绽放花蕾。她在自传中写道:
梦想与伤痛,如影随形。我告诉自己不能停,不能让伤痛掩盖梦想。
梦想与伤痛,如影随形。我告诉自己不能停,不能让伤痛掩盖梦想。
无论是场内追风,抑或纸上笔耕,以至在人生旅途上追寻梦想,或许只有承受痛苦的磨练,生命才能升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