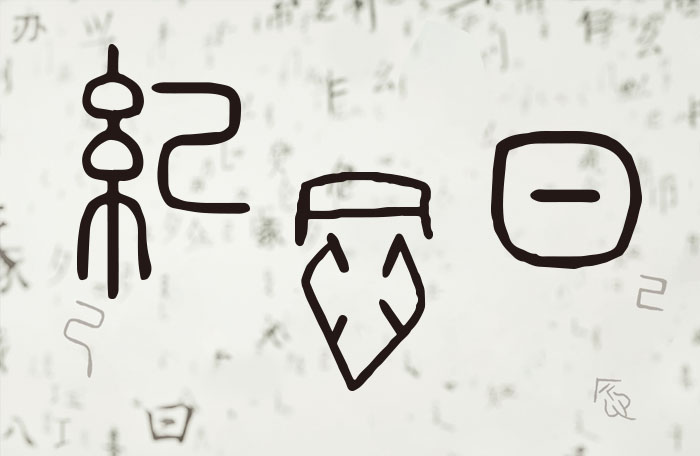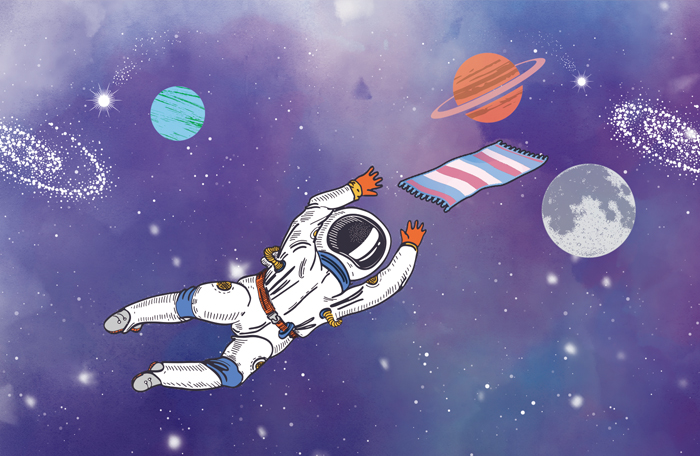圣诞刚过,春节马上又到了。逢年过节,少不免送礼。美国作家欧亨利(O. Henry)的经典之作《圣诞礼物》(The Gift of the Magi)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圣诞临近,一对贫穷的年轻夫妇为了送礼物给对方,一个剪掉秀发,换成金表链送予夫君;一个变卖家传金表,买下爱妻念念不忘的发饰。阴差阳错下,两人得物无所用。虽然如此,欧亨利却认为他们深谙送礼之道,智慧之高堪比东方三博士。
《圣诞礼物》写于一九零五年,故事中那对小夫妻假若生活在百多年后的今天,即使智慧再高,买礼物的烦恼也只会有增无减。今时今日,夫妻互送礼物的日子可不止于圣诞节。相识邂逅、表白定情、结婚周年……值得纪念的日子不胜枚举。香港作家朱少璋冷眼旁观,在〈发展感情这回傻事〉一文写道:“有了这批‘纪念日’作座标,感情就好像有了定点的发展根据和方向。”纪念日愈来愈受重视,甚至成为考验双方关系的小测大考。有些恋情才刚萌芽,便因某一方忘记纪念日而大大扣分;有一些岌岌可危的爱情,却凭纪念日的名贵礼物勉强过关。
纪念日无礼不欢的现象并非恋人所独有。现今社会,凡有节庆,似乎总要吃喝玩乐、互送礼物,才称得上尽兴。情人节纪念的是谁?圣诞节又有何意义?这些都在疯狂的促销抢购与热闹的觥筹交错间一一被人遗忘,纪念日仿佛就是为了购物、送礼、享乐而生。教宗方济各多次抨击圣诞节过度商业化,呼吁世人回归简朴生活,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对消费至上的节日文化同样深恶痛绝的,还有提倡设立母亲节的安娜 • 查维斯(Anna Jarvis)。
查维斯经历丧母之痛后,决定达成母亲的遗愿:指定一个日子来纪念天下的母亲,表扬她们的无私奉献。经她多方奔走,美国终于在一九一四年把每年五月第二个星期天(最接近查维斯母亲忌日的星期天)定为母亲节。
查维斯离乡工作,母女长期分隔两地,全赖一纸家书聊诉思念之情。她深明纸短情长的道理,鼓励人们在母亲节当天亲笔写信,赞颂亲恩。然而,当时大众庆祝母亲节,与其他节日一样,总离不开消费。与其花时间写信,何不干脆购买贺卡,在预印的词句旁边签名了事?查维斯批评道:“致送预印的贺卡,只代表你对为自己付出最多的人,连写点东西的心思都没有。”象征母亲节的白康乃馨平日乏人问津,但一到母亲节,价格便会飙升。当白康乃馨供不应求,花商便声称白康乃馨只适合纪念去世的母亲,若母亲健在,应赠以红康乃馨。母亲节日益商业化,查维斯不禁慨叹:“母亲节像圣诞等节庆一样,沦为礼物日,带来沉重压力,人人大洒金钱,造成诸多浪费,实非我们所乐见。”
到了二十一世纪,消费主义愈演愈烈。不少人以为在父亲节、母亲节当天与父母一起上馆子,送上名贵礼物,便是孝顺;在纪念日、节庆送礼给亲友,便能维系感情。事实上,父母也许更渴望子女陪伴左右;收礼者则为回礼费煞思量,最后人人家中都多了一些弃之可惜的无用之物。
难道表达心意一定得花钱吗?翻译家郑振铎种了两株石榴树,趁果实尚未熟透,用小刀刻上亲友和邻家孩子的名字。果子成熟后,他会找个星期天把孩子叫来,分发石榴,和他们一起玩游戏、说故事。原本平平无奇的星期天,从此变成大家翘首以待的“石榴节”,永志在这些孩子心中。

纪念日原是年历上一个平常日子,因记挂惦念而变得意义非凡;礼物本是生活中一件寻常物事,因浓情厚意而变得弥足珍贵。对《圣诞礼物》中那两口子来说,尽管表链和发饰失去了实际功用,却给予他俩携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希望。千里送鹅毛,礼轻情意重。只要赠物之人情真意切,哪怕微薄平凡如一颗石榴,已是最好的礼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