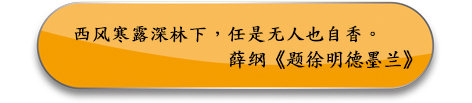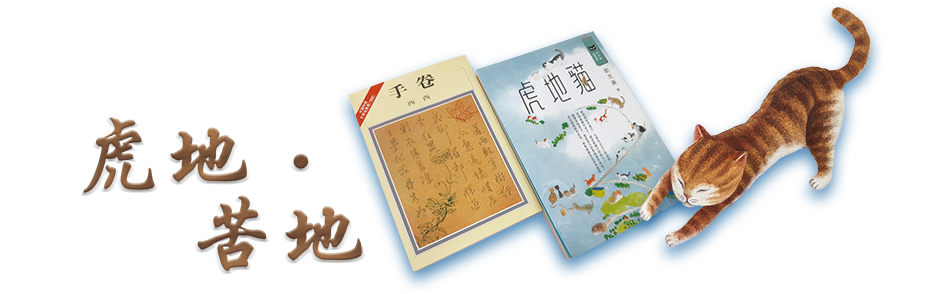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不少越南人乘船逃到香港,希望以难民身分移居其他国家。踏入八十年代,船民营不敷应用,屯门虎地军营用作安置越南船民,原可容纳二千九百人,却一度挤进四千多人。香港作家西西〈虎地〉一文(收录于短篇小说集《手卷》)描绘了越南船民在虎地禁闭营的生活。
九十年代,虎地的铁丝网随着营地关闭而拆除,又随着岭南学院兴建而筑起。铁丝网挡住了野犬,校园于是成了流浪猫栖息之地,后来再变为弃猫热点。二零一二年,台湾作家刘克襄到来担任驻校作家,发现校园内猫踪处处,于是昼夜观察,为猫儿拍照取名,分篇详述其独特习性,结集成纪实文学《虎地猫》。
〈虎地〉写的是人,《虎地猫》写的是猫,除地点相同外,两者看似并无关连,其实写的同是边缘一族的苦况。
西西笔下的滞港船民阿勇,十二岁时由父亲带到船上当杂工,谁知船出海后一去不回,漂流近两个月才抵达香港。六十人葬身海上,阿勇捡回一命,被送到虎地禁闭营,一住便是四年。营内尽是同胞,却无同根之谊,偷窃、打斗属等闲事。有人如愿转赴外国,有人毅然回乡。阿勇隐隐觉得父亲希冀自己走得更远,也就继续孤身苦守,以青春作赌注,博取移居的机会,苦候的日子过得像“死水一般滞留不动”。
“滞留不动”也是一些虎地猫的写照。校内中式庭园常有猫儿聚集,刘克襄称群居在此的猫为“余园集团”。牠们在园中徜徉,在墙头打盹,在池边晒太阳,生活看似写意,可是作者察觉到“池塘边展现过度拥挤的孤单,虎地猫在这儿明显自我退化”。猫儿日复日蹲守在善心人放食物的地方,“每只醒来就是在等吃,吃饱了便睡”,失去活力,不再好奇。由于进食浅纸盘,虎地猫易得传染病,没有主人悉心照顾,只能拖着病躯苟延残喘,时候到了,便找个隐蔽处躲起来,独自从这个世界消失。
身处如此苛刻境况,无论是越南船民抑或虎地猫,迎来新生命实在是忧多于喜。在〈虎地〉最后一节,西西藉着一名禁闭营护卫员的独白抒发感慨:这些年来难民营里“就生下了五千多个婴孩,平白又添了几千小难民”。《虎地猫》里,刘克襄发现母猫黑斑时常躲在下水道,原来是怀孕了。他虽盼望遇见黑斑的幼崽,但又不无忧虑:“只是迎接牠们的地面,恐怕会是更加严峻的环境。一个白亮的可怕世界。”
越南船民离乡背井,虎地猫遭主人抛弃,两者都离开了原来熟悉的地方。在刘克襄眼中,虎地猫曾被人豢养,跟大自然有了距离,“回不到那最原本的社会”,尽管“继续和人保持一紧密的连结,但某一程度又疏离了”。这用来形容离群漂泊者进退两难的窘境,也十分贴切。身在异乡,无依无靠, 命运往往系乎主流群体的态度。幸而这两部作品里的人物,一言一行皆流露恻隐之情,让读者在被迫直视冷酷现实之余,仍可感受到人世间几分暖意。
在〈虎地〉末节,护卫员谈起越南船民时,虽有提及他们对香港造成经济负担,却未有心生怨恨,反而充满怜悯:“活生生的人哪,怎能把船拖出公海去,让活生生的人都死在海上。”护卫员甚至不介意失去工作,但求船民早日安居。他豁达地说:“我宁愿所有的难民营都早点关闭,所有的难民都有地方收容。”
据《虎地猫》所述,岭南大学有很多爱猫之人,包括学生、行政人员、清洁工、护卫。他们定时放置猫粮,更有人带病猫看兽医。作者虽自言“习惯以自然观察的角度”,冷静客观地记录观察所得,可是当发现遭弃养的幼猫整天哀嚎,还是破例给牠买了罐头。凡此种种,让我们看到人性温暖善良的一面。
在〈虎地〉篇末,西西透过故事人物,阐述“虎地”与 “苦地”的联想:
……(铁丝网)真是一件奇异的东西,连你,连我,也好像给它围在里面了。所有的人站立的地方,都是铁丝网围着的小小的一片苦地啊。
……(铁丝网)真是一件奇异的东西,连你,连我,也好像给它围在里面了。所有的人站立的地方,都是铁丝网围着的小小的一片苦地啊。
或许凭借一点善念,就能穿透人与人之间那道铁丝网,使苦地化为乐土,让飘零者暂得安身立命之所,就像刘克襄笔下那只在屋顶上翻露肚皮、舔毛的猫,饱足自在,得享片刻安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