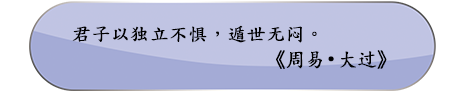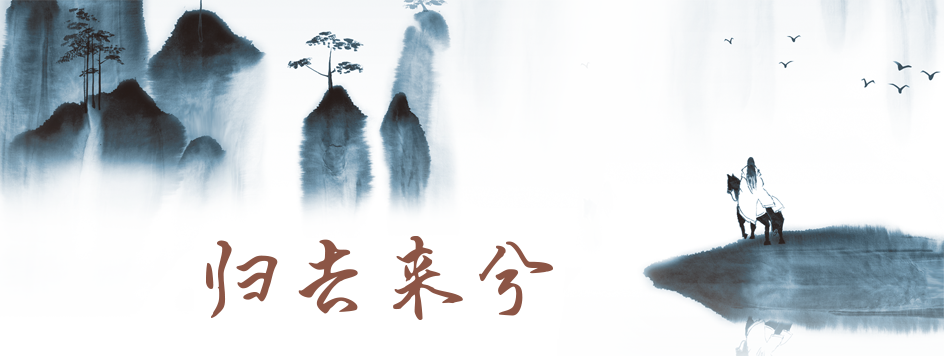
古代士人胸怀经世济民的抱负,向来学而优则仕。然而,当为政者昏庸无道,未来一片黯淡,读书人又该如何自处?孔子有言: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”出仕还是隐逸?且看商朝的伯夷和叔齐、三国时期的阮籍、元朝的张养浩如何抉择。
伯夷和叔齐是商朝孤竹国王子,孤竹君生前属意立三子叔齐为新君。父亲死后,叔齐认为依礼应由长兄伯夷继位,伯夷却以父命难违为由而拒绝。兄弟互相推让,先后离开孤竹,欲投奔西伯姬昌。谁知到达周国时,姬昌已病故。两人见其子武王正载着其灵位发兵伐纣,于是拉停马匹劝谏说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弒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将士勃然大怒,挥刀就想把这两个胡言乱语的老头子给砍了,幸得姜太公在旁说项,两人才得以活命。不久武王灭纣,建立周朝,天下莫不归服,伯夷、叔齐却引以为耻,不食周粟,隐居于首阳山,采薇充饥,最后双双饿死。
史书记载商纣王残暴不仁,武王伐纣是顺应天道,人心所归,而周武王的儿孙也的确开创了成康盛世,可是伯夷、叔齐“举世非之,力行而不惑”,坚持以暴易暴非君子所为,宁愿饿死深山,也不踏足他们眼中的无义之地。司马迁有感于“末世争利,维彼奔义;让国饿死,天下称之”,把二人事迹冠于《史记》七十列传之首。不过,他们这种螳臂当车式的孤勇,并非人人欣赏。三国魏文学家阮籍作《首阳山赋》,批评伯夷、叔齐连生死也不顾,却偏执于褒贬毁誉;如果真的不求闻达,何必多有言辞?与其满怀愤激,不如无所欲求,清虚自守。
阮籍位列竹林七贤之首,《晋书》形容他“本有济世志”,无奈当时正值魏晋权力更迭之际,“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。”何晏、夏侯玄、嵇康……一个个良才俊彦被卷入曹魏与司马氏之间的权力斗争,惨成刀下亡魂。阮籍不想同流合污,但因亡父属曹魏阵营,自己又才名在外,成为两方极力拉拢的对象。阮籍无奈入仕后,整天纵酒谈玄,淡泊名利,奉行“大隐隐于朝”之道。
阮籍性格充满矛盾。他一方面蔑视礼法:无视当时“嫂叔不通问”的礼教大防,主动与归宁的嫂子话别;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,便大剌剌地躺在貌美的老板娘身旁;听闻有才色双全的佳人香消玉殒,即使与其父兄素昧平生,也上门恸哭哀悼。另一方面,这名任诞不羁的狂士在政治上却十分谨慎,从不谈论时事、臧否人物,说话玄之又玄。其挚友嵇康说他“口不论人过,吾每师之而未能及”。
身处险恶的政治漩涡之中,“清虚以守神”终究只是奢望。阮籍常独自驾车漫行,行至尽头,便“痛哭而返”。权臣当道,壮志未酬,既无意仿效伯夷和叔齐伏节死义,就连披发入山也成妄想,除了途穷而哭,抒发郁闷愤懑之情,还能如何排遣?景元四年,阮籍被迫为野心勃勃的司马昭写《劝进表》,写毕后不久便郁郁而终。
十三世纪,蒙古铁骑入主中原,绵延三百多年的宋朝黯然落幕。在重武轻文、歧视汉人的元代,有一位汉族文人官至礼部尚书,死后追封为滨国公。这个异数便是发出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”这声千古喟叹的张养浩。
张养浩勤政爱民,官拜监察御史后,更是弹劾不避权贵。其《牧民忠告》、《风宪忠告》、《庙堂忠告》皆为后世仕宦案头必备。张养浩为官多年,厌倦了宦海的龌龊和虚伪,遂罢官而去。他隐居济南老家八年,与青山绿水为伴,笔下诗文散曲尽显愉悦之情:“云霞,我爱山无价。看时行踏,云山也爱咱。”朝廷多次征召,都不为所动。
张养浩虽然高唱“说着功名事,满怀都是愁,何似青山归去休。休,从今身自由”,但在百姓受灾时,还是挺身而出。天历二年,关中大旱,饥民相食,朝廷任命他为陕西行台中丞。这次他没有推辞,立即上任前往赈灾,四个月间,吃住皆在公署,夙兴夜寐,救济灾民,结果积劳成疾,卒于任上。史籍记载:“关中之人,哀之如失父母。”
士大夫因性情所至,形势所迫,或以死明志,或纵酒佯狂,或徘徊于山林庙堂之间,示范了何谓匹夫之志不可夺。历朝史册满纸尔虞我诈,腥风血雨,尤幸仍可看见这些特立独行之士伟岸的身影。他们高风亮节、一片丹心,在浩瀚史海里散发柔而不弱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