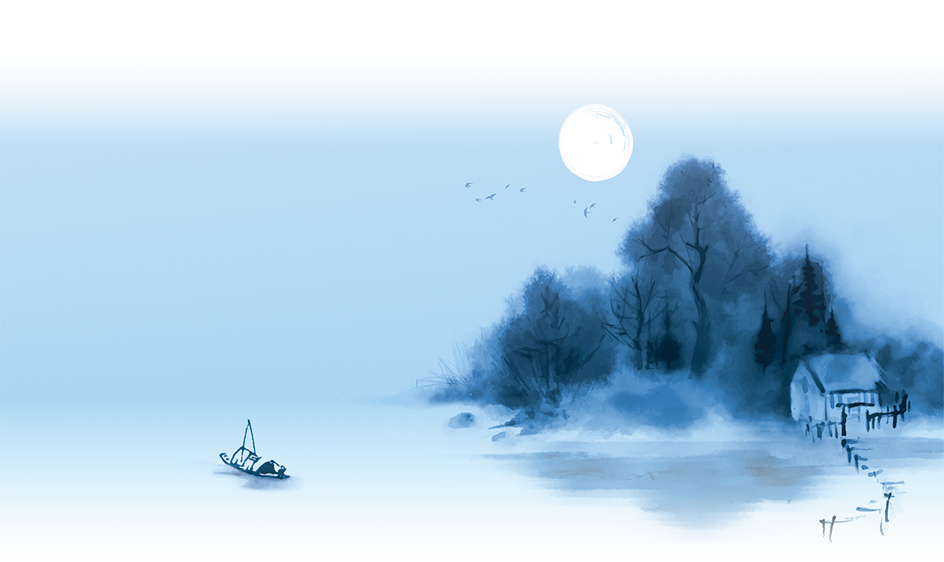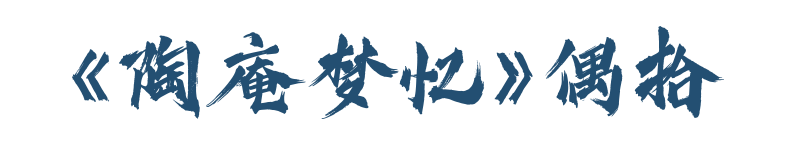
署理高级法定语文主任吴颂祺
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隆冬时节,连下三天瑞雪。久雪乍停,张岱驾一叶小舟,独往湖心亭看雪。西子湖上,不闻人鸟声。山水烟云,白茫茫一片,仿如置身于丹青水墨之中,只见点点墨痕。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〈湖心亭看雪〉一文,写活数百年前那清寂雪夜的痴人痴行。
先生何许人也?张岱,字宗子,号陶庵,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,出身官宦世家。高祖张天复,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;祖父张汝霖为江西布政使司参议。他自言早岁为纨袴子弟,纵情声色犬马,极尽浮靡,明亡后家财散尽,但坚拒仕清,甘作遗民,潜心修书。
张岱隐居深山,粗衣粝食,常至断炊,忆前朝流金岁月,恍若黄粱一梦。故人故国难忘,遂奋笔为文,记下昔日情怀,聊以自慰。他于《陶庵梦忆》序中自道:“偶拈一则,如游旧径,如见故人,城郭人民,翻用自喜,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。”虽知大梦将寤,惟求名之心不息,犹望笔下片言只字得以流传久永。
陶庵先生是个痴人,也是个妙人。他既爱在万籁俱寂的冬夜,观赏静谧空灵的山水雪景,也爱在人流如潮的节日,细察熙攘喧嚣的市井人情。且看他在〈西湖七月半〉如何以诙谐笔触勾勒中元节赏月者的众生相:
其一,亦船亦楼,名娃闺秀,携及童娈,笑啼杂之,环坐露台,左右盼望,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,看之。其一,亦船亦声歌,名妓闲僧,浅斟低唱,弱管轻丝,竹肉1相发,亦在月下,亦看月,而欲人看其看月者,看之。
其一,亦船亦楼,名娃闺秀,携及童娈,笑啼杂之,环坐露台,左右盼望,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,看之。其一,亦船亦声歌,名妓闲僧,浅斟低唱,弱管轻丝,竹肉1相发,亦在月下,亦看月,而欲人看其看月者,看之。
有人身在月下却无心看月,左顾右盼;亦有人虽在看月,却也希望人家看他赏月。凡此种种,显见是俗人所为,教人啼笑皆非。待游人散去,张岱始与友人泛舟对酌。夜静人稀的西湖,“月如镜新磨,山复整妆,湖复颒面”,另有一番景致。及至东方既白,众人率性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,任由小舟在湖面飘荡,浑然忘机。
世家子弟多深谙丝竹管弦之道,张岱自不例外。中年后家道由盛入衰,历尽劫难,忆起昔日天籁,不啻久旱逢甘露。他在〈虎丘中秋夜〉一文,描写虎丘中秋曲会盛况。曲会初开,游人众多,有如“雁落平沙,霞铺江上”,只听见鼓乐喧天,丝竹繁兴,人人和唱,纵使不辨节拍,仍然自得其乐。古人有“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”之说,对清唱推崇备至。若想在虎丘曲会欣赏最纯粹的歌艺,也得像观看西湖夜景般,待至更深夜残,人潮消散,俗乐渐歇,其时“一夫登场,高坐石上”,四周“不箫不拍”,已无乐器伴奏。唱者“声出如丝,裂石穿云,串度抑扬,一字一刻”。听者如痴如醉,心动神驰,“不敢击节,惟有点头”。时值三更,犹有百余人恋恋不舍。只要功深艺湛,哪怕曲高和寡,天寥地寂,也可觅得知音。
综观《陶庵梦忆》诸篇,对前朝金粉着墨最多者,当推〈扬州清明〉。张岱以生动精彩的文笔,记录清明时节扬州的风貌:
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、曲中名妓,一切好事之徒,无不咸集。长塘丰草,走马放鹰;高阜平冈,斗鸡蹴踘;茂林清樾,劈阮弹筝。浪子相扑,童稚纸鸢,老僧因果,瞽者说书。立者林林,蹲者蛰蛰。
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、曲中名妓,一切好事之徒,无不咸集。长塘丰草,走马放鹰;高阜平冈,斗鸡蹴踘;茂林清樾,劈阮弹筝。浪子相扑,童稚纸鸢,老僧因果,瞽者说书。立者林林,蹲者蛰蛰。
城中名流巨贾、贩夫走卒,以至僧人游民,诸般情状,活灵活现,如在目前。文末笔锋一转,从都市浮华联想到《清明上河图》:“南宋张择端作《清明上河图》,追摹汴京景物,有西方美人之思2,而余目盱盱,能无梦想!”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,以工笔描绘汴京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俗,还原北宋都城的繁华旧貌。张岱望风怀想,追慕故国。一册《陶庵梦忆》,把所梦所想诉诸文字,也留住了晚明一道人间烟火。
张岱历经繁华,也阅尽沧桑。多舛的命运,恣意的才情,造就了千古美文。《陶庵梦忆》文采华茂,哲思深邃,宛若夜空中璀璨的明星,绽放异彩,光耀文坛。
1 “竹”指竹制的管乐器,“肉”指歌喉。
2 《诗经》以“西方美人”比喻周室圣王,后以“西方美人之思”指怀念故国。
1 “竹”指竹制的管乐器,“肉”指歌喉。
2 《诗经》以“西方美人”比喻周室圣王,后以“西方美人之思”指怀念故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