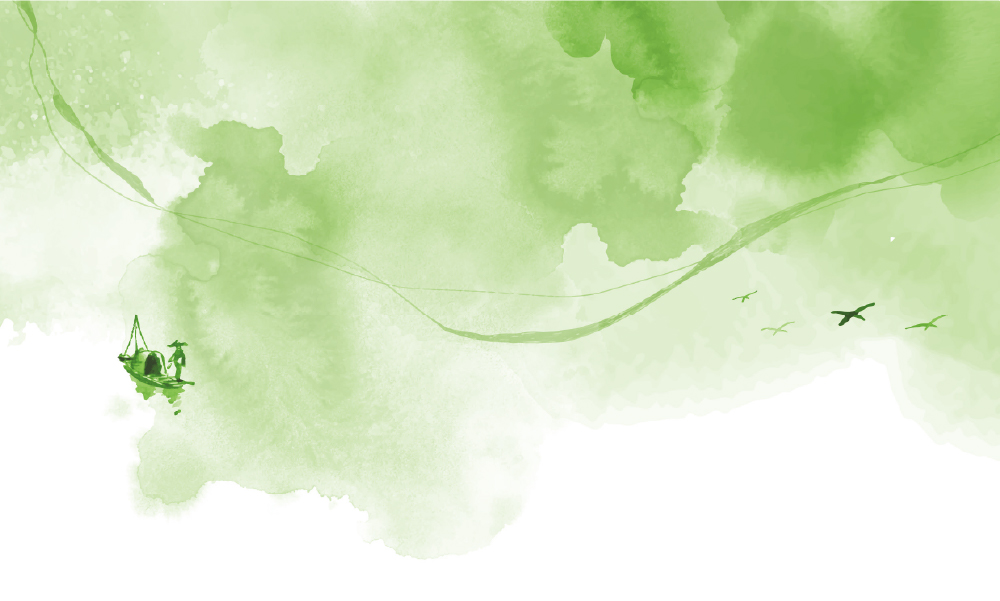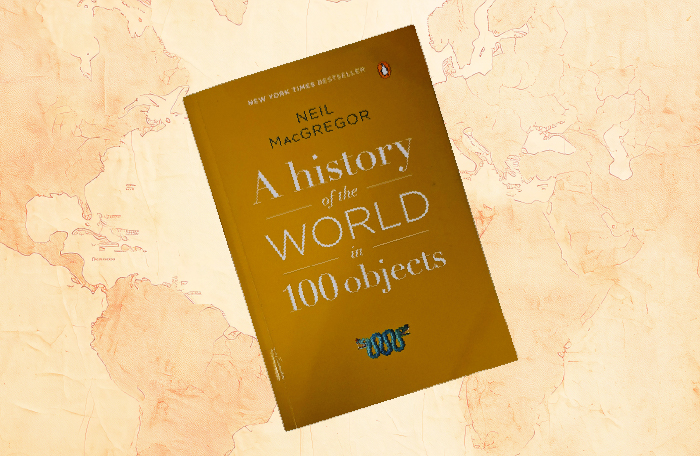明人袁宏道说:“人情必有所寄,然后能乐。”清人张潮亦云:“人不可以无癖。”人若没有癖好,对什么都不感兴趣,生活不免索然乏味。王子猷呼竹为君,米元章拜石为丈,王世贞嗜书如命,无非为求一晌清欢而寄情于物。然而,若过分沉湎其中而不得自在,癖好反会成为心灵枷锁。
《世说新语•雅量》有一则关于癖好的轶事:东晋名将祖逖之弟祖约,平日贪财爱货,与闻鸡起舞、中流击楫的兄长截然不同。某日,祖约正在赏玩财物,忽然有客临门。他赶忙收拾,东塞西藏之际,客人已至,还有两个小竹簏未及收好,唯有侧身挡住,一脸慌张尴尬。他的同僚阮孚乃竹林七贤之一阮咸之子,不仅嗜酒成癖,还爱收藏木屐。有人拜访阮孚,见他神色闲畅,吹火熔蜡,一边给木屐上蜡,一边悠悠而叹:“未知一生当着几量注屐?”在晋人看来,爱财和爱屐并无高下之分,关键在于能否处之泰然。从阮祖二人的反应来看,谁的境界更高,不言而喻。
大文豪苏轼也是个收藏家,尤爱藏砚蓄墨,对于“祖财阮屐”这个故事颇有感触。他在《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》一诗写道:“世间有癖念谁无,倾身障簏尤堪鄙。人生当着几两注屐,定心肯为微物起。”嗜癖虽属人之常情,也要适可而止。人生苦短,若为物役,岂非自缚?苏轼的老乡石昌言爱墨,舍不得磨名家之墨;好友李公择也嗜墨,亲友的好墨都被他夺去,屋里挂满墨条。二人如守财奴般得物而不用,东坡先生感叹这实在是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。
熙宁十年,驸马王诜建宝绘堂藏书画,邀苏轼为文作记。苏轼在《宝绘堂记》忠告友人: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,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”欣赏物事之美以寄情趣,当须超然其外,方得自乐。若过度耽溺,反受其害。苏轼忆述自己年少时好书画,自己有的,生怕失去;别人有的,惟恐得不到。后来幡然醒悟:“吾薄富贵而厚于书,轻死生而重于画,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?”自此视书画为过眼烟云,得之固喜,失之不念,才得以重拾乐趣。
随着年岁渐长,阅历益丰,人往往反思自身与物事之间的依存关系。苏轼如是,李清照亦然。李清照年轻时,与丈夫赵明诚一同收藏书画金石,助他完成巨著《金石录》。她晚年在《金石录》后序中坦言,癖好“名虽不同,其惑一也”,无论是钱财抑或书册,皆为惑人心志之物。这位曾为购古玩不惜典当衣物的才女,何以如此感叹?
赵明诚与李清照住在青州老家那些年,收书甚丰。赵明诚把书册锁于书库,每次取阅都须先开锁,再登记,对藏书呵护备至。书本稍有污损,他就会叫妻子清理涂改。李清照不堪其扰,索性节衣缩食,另购副本自用。藏书本求适意,如今反添烦厌,或许这时她也如苏轼般,兴起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之慨。
靖康之变后,衣冠南渡。二人珍爱之物,大多被迫割舍。建炎三年,赵明诚获授官,往建康受命。临别时,李清照急切问道:“如传闻城中缓急,奈何?”赵明诚答道:“从众,必不得已,先去辎重,次衣被,次书册卷轴,次古器,独所谓宗器者,可自负抱,与身俱存亡,勿忘也。”言毕,便策马而去。兵荒马乱之际,枕边人竟要求自己以藏品为重,甚至与宗庙礼器共存亡。那一刻,李清照想必百感交集。
江边一别后不久,赵明诚便因病遽逝。李清照孤身带着金石书画继续往南,一路颠沛流离,身边的文物丢弃的、毁于战火的、被盗的、怯于流言而献给朝廷的,十之七八,最后只剩下一两部残破不全的书册,与三数种价值不高的书帖。
饱经风霜后,李清照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因为买不到《牡丹图》而惆怅数日的少妇,此时的她甚至比苏轼看得更通透豁达。她以自己大半生的忧患得失,劝诫“后世好古博雅者”:“有有必有无,有聚必有散,乃理之常。人亡弓,人得之,又胡足道!”
李清照这番肺腑之言,不仅让好古博雅者引以为戒,常人也可借镜。谁家中没有一大堆满载回忆的旧物?然而,日积月累,旧物渐成负担,致使人为物累,心为形役。“人亡弓,人得之。”那些曾与我们相伴的物件,终究会随缘分散,流转到别人手中,或受珍爱,或被遗忘。万物聚散有时,又何须耿耿于怀?
注:“量”、“两”通“緉”(緉,古代计算鞋的单位),“几緉”即“几双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