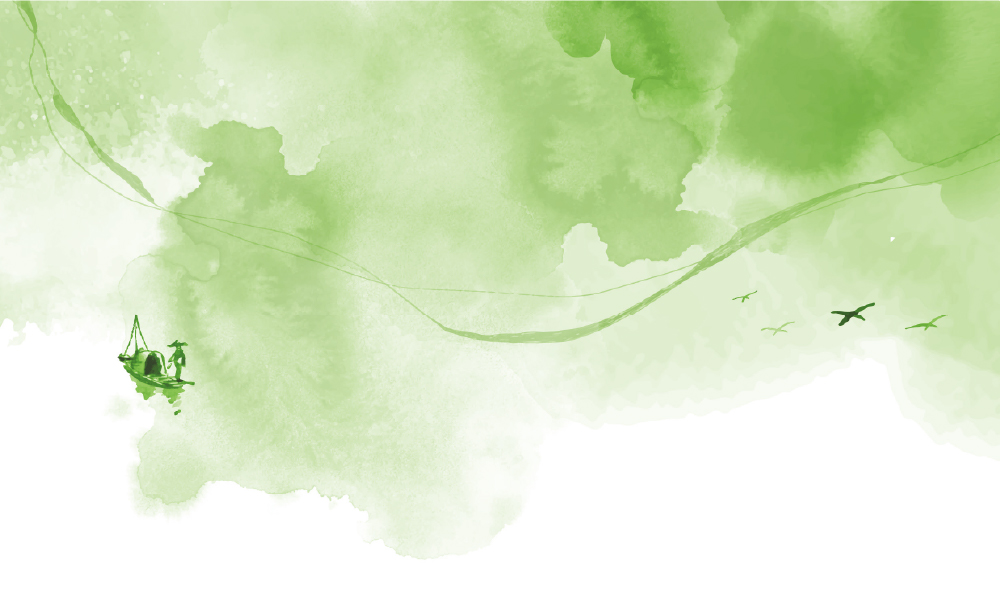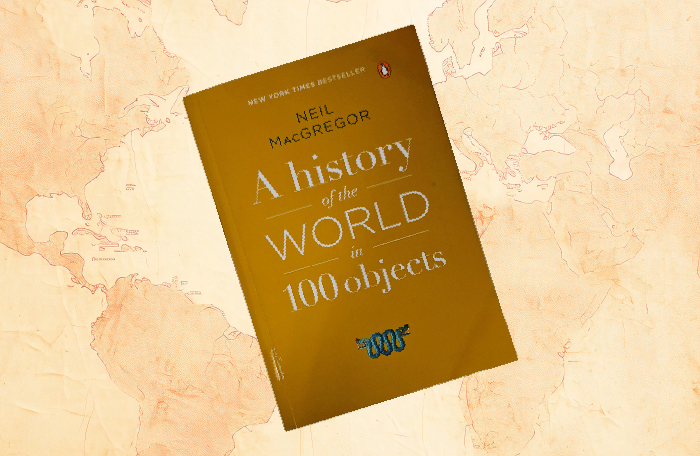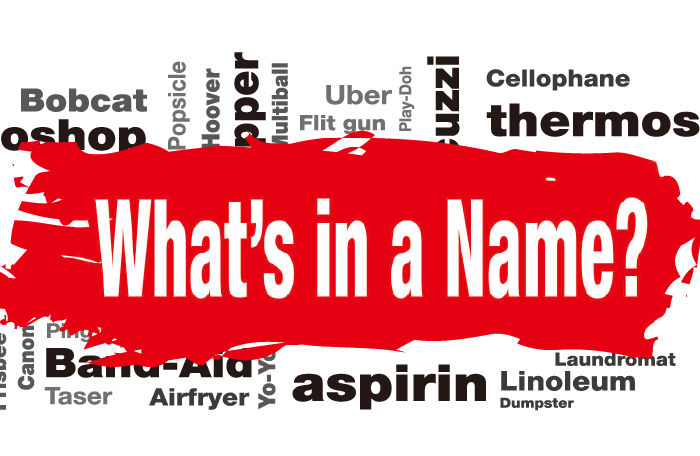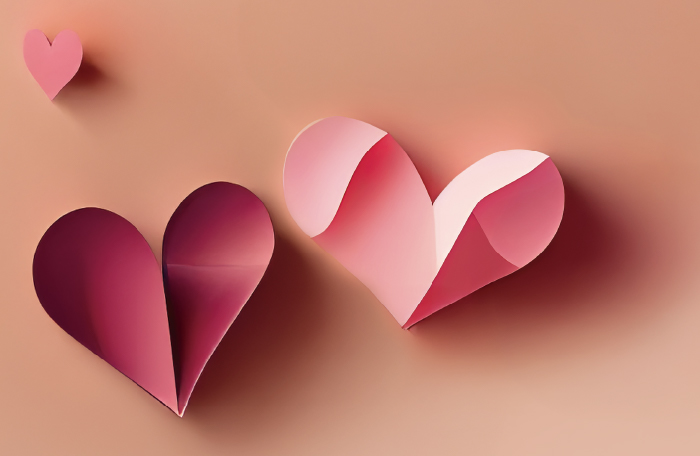明人袁宏道說:“人情必有所寄,然後能樂。”清人張潮亦云:“人不可以無癖。”人若沒有癖好,對什麼都不感興趣,生活不免索然乏味。王子猷呼竹為君,米元章拜石為丈,王世貞嗜書如命,無非為求一晌清歡而寄情於物。然而,若過分沉湎其中而不得自在,癖好反會成為心靈枷鎖。
《世說新語•雅量》有一則關於癖好的軼事:東晉名將祖逖之弟祖約,平日貪財愛貨,與聞雞起舞、中流擊楫的兄長截然不同。某日,祖約正在賞玩財物,忽然有客臨門。他趕忙收拾,東塞西藏之際,客人已至,還有兩個小竹簏未及收好,唯有側身擋住,一臉慌張尷尬。他的同僚阮孚乃竹林七賢之一阮咸之子,不僅嗜酒成癖,還愛收藏木屐。有人拜訪阮孚,見他神色閒暢,吹火熔蠟,一邊給木屐上蠟,一邊悠悠而歎:“未知一生當着幾量註屐?”在晉人看來,愛財和愛屐並無高下之分,關鍵在於能否處之泰然。從阮祖二人的反應來看,誰的境界更高,不言而喻。
大文豪蘇軾也是個收藏家,尤愛藏硯蓄墨,對於“祖財阮屐”這個故事頗有感觸。他在《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》一詩寫道:“世間有癖念誰無,傾身障簏尤堪鄙。人生當着幾兩註屐,定心肯為微物起。”嗜癖雖屬人之常情,也要適可而止。人生苦短,若為物役,豈非自縛?蘇軾的老鄉石昌言愛墨,捨不得磨名家之墨;好友李公擇也嗜墨,親友的好墨都被他奪去,屋裏掛滿墨條。二人如守財奴般得物而不用,東坡先生感歎這實在是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。
熙寧十年,駙馬王詵建寶繪堂藏書畫,邀蘇軾為文作記。蘇軾在《寶繪堂記》忠告友人:“君子可以寓意於物,而不可以留意於物。”欣賞物事之美以寄情趣,當須超然其外,方得自樂。若過度耽溺,反受其害。蘇軾憶述自己年少時好書畫,自己有的,生怕失去;別人有的,惟恐得不到。後來幡然醒悟:“吾薄富貴而厚於書,輕死生而重於畫,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?”自此視書畫為過眼煙雲,得之固喜,失之不念,才得以重拾樂趣。
隨着年歲漸長,閱歷益豐,人往往反思自身與物事之間的依存關係。蘇軾如是,李清照亦然。李清照年輕時,與丈夫趙明誠一同收藏書畫金石,助他完成巨著《金石錄》。她晚年在《金石錄》後序中坦言,癖好“名雖不同,其惑一也”,無論是錢財抑或書冊,皆為惑人心志之物。這位曾為購古玩不惜典當衣物的才女,何以如此感歎?
趙明誠與李清照住在青州老家那些年,收書甚豐。趙明誠把書冊鎖於書庫,每次取閱都須先開鎖,再登記,對藏書呵護備至。書本稍有污損,他就會叫妻子清理塗改。李清照不堪其擾,索性節衣縮食,另購副本自用。藏書本求適意,如今反添煩厭,或許這時她也如蘇軾般,興起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之慨。
靖康之變後,衣冠南渡。二人珍愛之物,大多被迫割捨。建炎三年,趙明誠獲授官,往建康受命。臨別時,李清照急切問道:“如傳聞城中緩急,奈何?”趙明誠答道:“從眾,必不得已,先去輜重,次衣被,次書冊卷軸,次古器,獨所謂宗器者,可自負抱,與身俱存亡,勿忘也。”言畢,便策馬而去。兵荒馬亂之際,枕邊人竟要求自己以藏品為重,甚至與宗廟禮器共存亡。那一刻,李清照想必百感交集。
江邊一別後不久,趙明誠便因病遽逝。李清照孤身帶着金石書畫繼續往南,一路顛沛流離,身邊的文物丟棄的、毀於戰火的、被盜的、怯於流言而獻給朝廷的,十之七八,最後只剩下一兩部殘破不全的書冊,與三數種價值不高的書帖。
飽經風霜後,李清照已不再是當年那個因為買不到《牡丹圖》而惆悵數日的少婦,此時的她甚至比蘇軾看得更通透豁達。她以自己大半生的憂患得失,勸誡“後世好古博雅者”:“有有必有無,有聚必有散,乃理之常。人亡弓,人得之,又胡足道!”
李清照這番肺腑之言,不僅讓好古博雅者引以為戒,常人也可借鏡。誰家中沒有一大堆滿載回憶的舊物?然而,日積月累,舊物漸成負擔,致使人為物累,心為形役。“人亡弓,人得之。”那些曾與我們相伴的物件,終究會隨緣分散,流轉到別人手中,或受珍愛,或被遺忘。萬物聚散有時,又何須耿耿於懷?
註:“量”、“兩”通“緉”(緉,古代計算鞋的單位),“幾緉”即“幾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