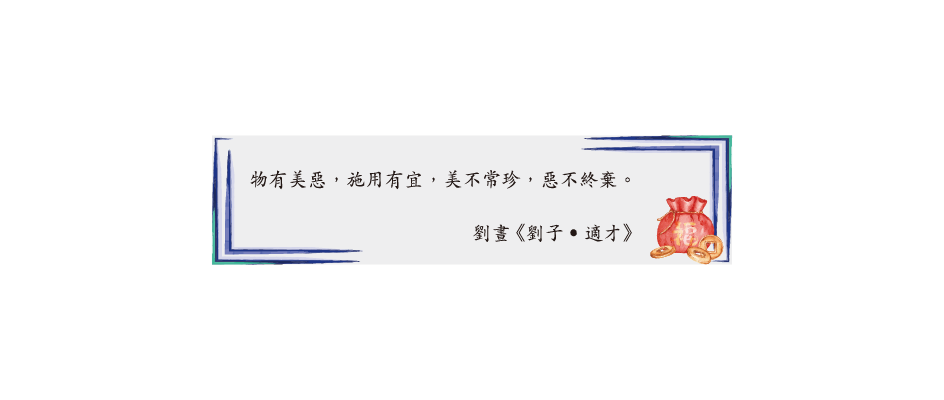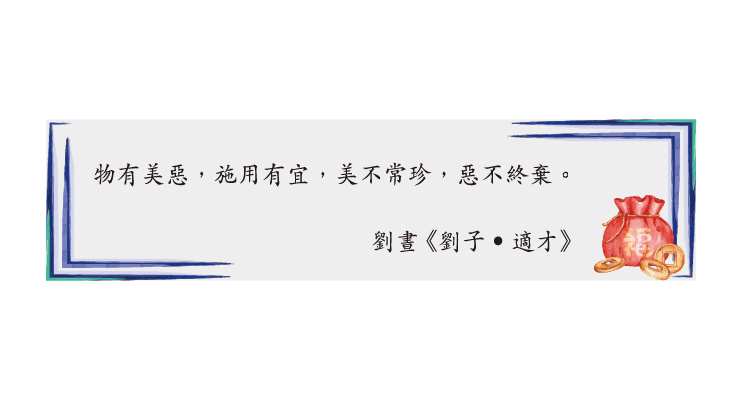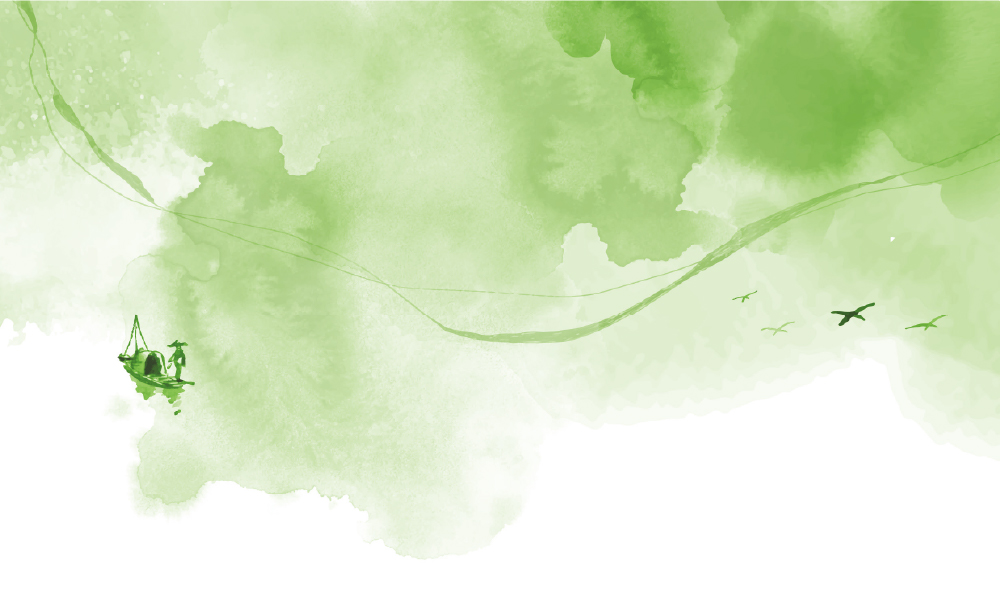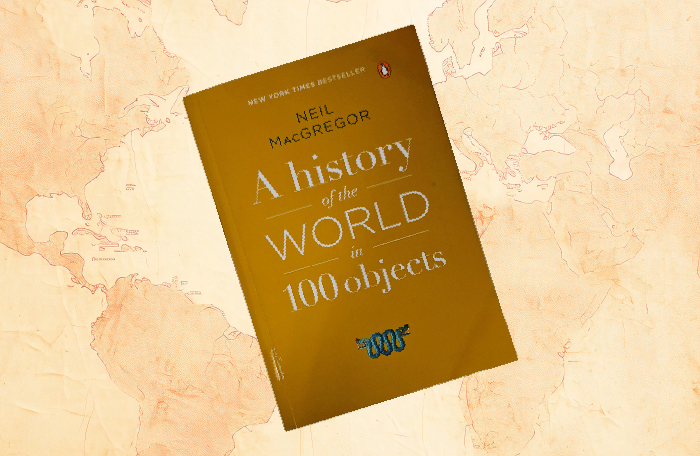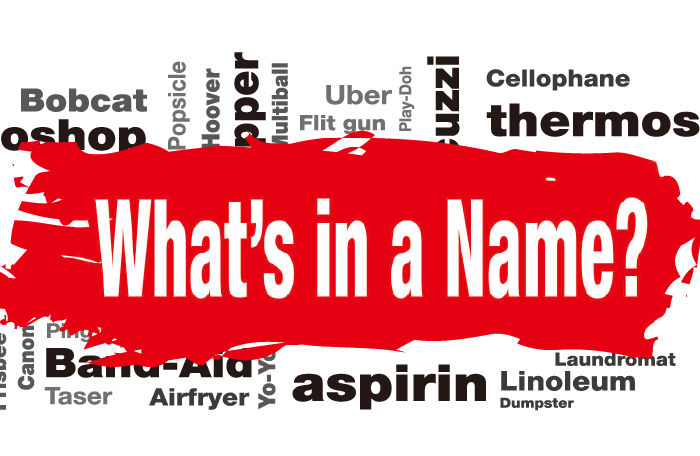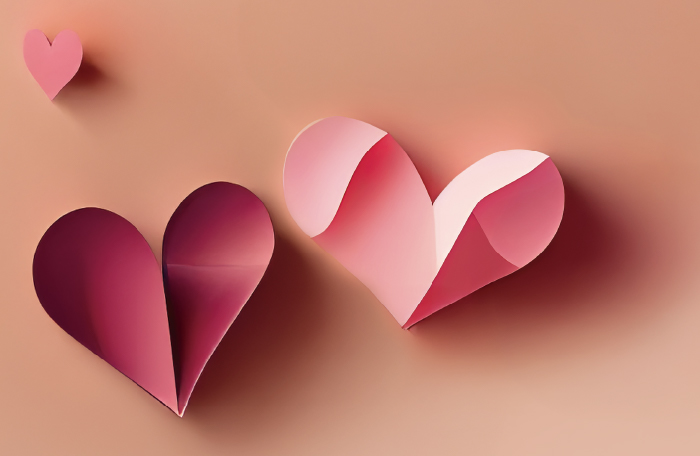清代桐城名士姚元之《竹葉亭雜記》載述了這樣一則軼事:某年除夕,姚元之到座師朱珪家拜年,閒談間“問公歲事如何”,老先生舉起胸前荷包打趣說:“可憐此中空空,壓歲錢尚無一文也。”不久,僕人來報:“門生某爺某爺節儀若干封。”朱珪戲謔:“此數人太呆,我從不識其面,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!”朱珪為人清廉,嘉慶帝稱其“一世不談錢”,給他送錢可不正是“阿堵物付流水”,即俗語所謂“抌錢落鹹水海”?
錢為何稱作“阿堵物”?這得從另一位同樣不談錢的古人說起。《世說新語•規箴》記載,魏晉末年重臣王衍崇尚清談,自命清高,尤其討厭妻子貪財俗氣。王衍為顯高雅,從不說一個“錢”字。王夫人趁他熟睡時着人把錢撒滿牀邊,讓他沒法下牀,心想這樣他就不得不說個“錢”字了。豈料王衍醒來,只呼令僕人把地上的東西拿走:“舉卻阿堵物!”“阿堵”為當時口語,意為“這個”,“阿堵物”即“這個東西”。從此,“阿堵物”便成了錢的別稱。
王衍出身高門望族,位至宰執,自有清高的本錢。東晉學者王隱所言一針見血:“……求富貴得富貴,資財山積,用不能消,安須問‘錢’乎?而世以不問為高,不亦惑乎!”王衍連說個“錢”字也怕弄髒嘴巴,時人隱士魯褒非但毫不避忌,還特地寫了一篇《錢神論》,把外圓內方的銅錢戲稱為“孔方”,譏諷世人對之“親愛如兄”。文章如此描述錢可通神的社會現象:“錢之所在,危可使安,死可使活;錢之所去,貴可使賤,生可使殺……夫錢,窮者能使通達,富者能使溫暖,貧者能使勇悍。”《錢神論》問世後,“疾時者共傳其文”,“孔方兄”這個稱呼不脛而走,流播後世。
有了“阿堵物”和“孔方兄”這些別稱,文人騷客提及錢的時候,頓時少了一點銅臭,多了幾分雅致。沒錢喝酒,是“愛酒苦無阿堵物,尋春奈有主人家”(張耒《和无咎》之二);年關難過,是“阿堵元知不受呼,忍貧閉戶亦良圖”(陸游《歲暮貧甚戲書》);“錢”途無望,是“管城子無食肉相,孔方兄有絕交書”(黃庭堅《戲呈孔毅父》);世態炎涼,是“有堪使鬼原非謬,無任呼兄亦不來”(沈周《詠錢》之二)。
天下熙熙,皆為利來;天下攘攘,皆為利往。為了錢,有人背信棄義,有人不擇手段。歷代不乏控訴萬惡金錢的詩文。唐詩人羅隱《錢》一詩痛罵金錢顛倒了世道:“志士不敢道,貯之成禍胎。小人無事藝,假爾作梯媒。解釋愁腸結,能分睡眼開。朱門狼虎性,一半逐君回。”南宋李之彥在《東谷所見》感歎“金旁著兩戈字,真殺人之物”。清狂士戴名世的雜文《錢神問對》則謂自金錢流傳人間,惑亂民志,以致萬惡俱起:“天下之死於汝手者,不可勝數也!”
錢若有靈,定必感到萬般委屈。它無非是經濟發展的產物,又何罪之有?錢是善是惡,全在用者的抉擇。當家方知柴米貴,盛唐名相張說為政數十年,深諳“倉廩實而知禮節,衣食足而知榮辱”之理,對錢倒不是一味鄙夷。他的雜文《錢本草》以錢喻作藥,論其利弊得失,妙趣橫生:
錢,味甘,大熱有毒,偏能駐顏,彩澤流潤,善療飢寒困厄之患,立驗。能利邦國,污賢達,畏清廉。貪婪者服之,以均平為良;如不均平,則冷熱相激,令人霍亂。其藥采無時,采至非理則傷神。此既流行,能役神靈,通鬼氣。如積而不散,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;如散而不積,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。一積一散謂之道,不以為珍謂之德,取與合宜謂之義,使無非分謂之禮,博施濟眾謂之仁,出不失期謂之信,入不妨己謂之智,以此七術精鍊方可。久而服之,令人長壽。若服之非理,則弱志傷神,切須忌之。
錢,味甘,大熱有毒,偏能駐顏,彩澤流潤,善療飢寒困厄之患,立驗。能利邦國,污賢達,畏清廉。貪婪者服之,以均平為良;如不均平,則冷熱相激,令人霍亂。其藥采無時,采至非理則傷神。此既流行,能役神靈,通鬼氣。如積而不散,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;如散而不積,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。一積一散謂之道,不以為珍謂之德,取與合宜謂之義,使無非分謂之禮,博施濟眾謂之仁,出不失期謂之信,入不妨己謂之智,以此七術精鍊方可。久而服之,令人長壽。若服之非理,則弱志傷神,切須忌之。
張說的馭錢七術,放諸今日仍能振聾發聵。從古時“有錢堪使鬼”到今天“有錢能使鬼推磨”,孔方兄的威力千載不減。新春將至,又到了孩子喜滋滋領利是的時候。何不把握良機,教導孩子養成量入為出的好習慣,又或鼓勵他們把部分利是錢捐給有需要的人?利是豐收的喜悅會隨春節結束而淡卻,真正讓孩子受用一生的無價之寶,並非銀行帳戶裏那串冷冰冰的數字,而是正確的金錢觀和仁善之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