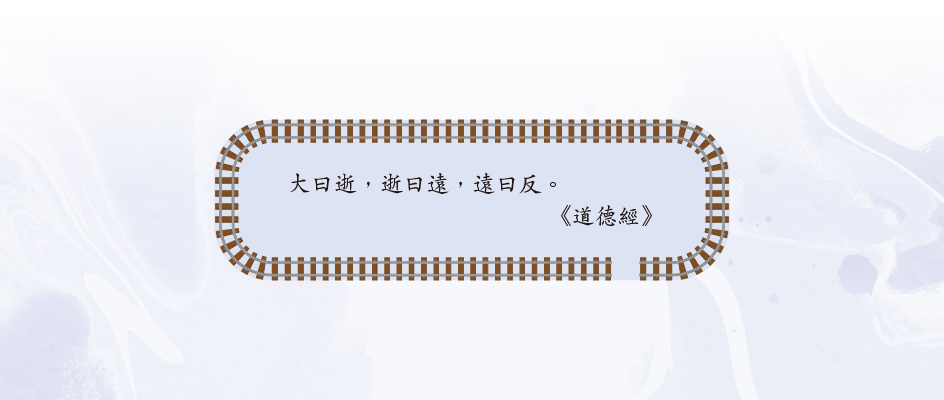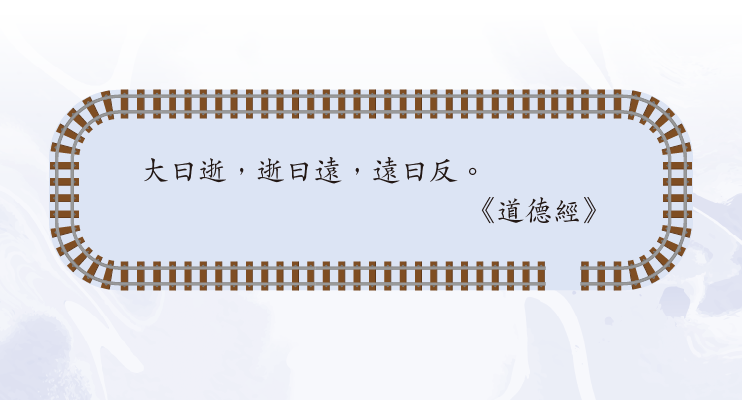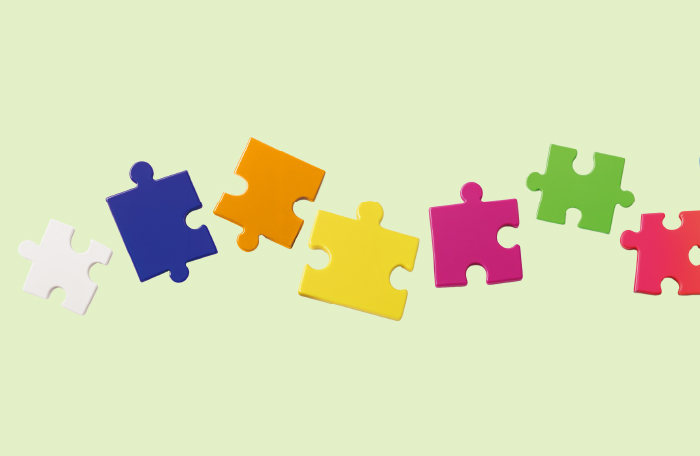先生自己也唸書。後來,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,靜下去了,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:
“鐵如意,指揮倜儻,一座皆驚呢──;金叵羅,顛倒淋漓噫,千杯未醉呵──”
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,因為讀到這裏,他總是微笑起來,而且將頭仰起,搖着,向後面拗過去,拗過去。
先生自己也唸書。後來,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,靜下去了,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:
“鐵如意,指揮倜儻,一座皆驚呢──;金叵羅,顛倒淋漓噫,千杯未醉呵──”
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,因為讀到這裏,他總是微笑起來,而且將頭仰起,搖着,向後面拗過去,拗過去。
魯迅在散文《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》中,回想年少時跟隨塾師壽鏡吾讀書的情景。老師搖頭擺腦,讀到“驚”、“漓”、“醉”等字還特意拉長腔調。少年魯迅似懂非懂,也能從先生那自得其樂的樣子,感受到文章的魅力。

豐子愷漫畫
讓魯迅數十年不忘的朗讀聲,是漢詩文的傳統讀法,包含唱、吟、詠、哦、歎、誦等多種形式,後來為免與現代朗讀混淆,改稱為“中華吟誦”,簡稱“吟誦”。吟誦者依字行腔,依義行調,結合個人體會,圓融流轉地讀出詩文,表達千般情致,或蒼涼慷慨,或清越婉轉,或沉鬱激盪,或深邃悠長。千百年來,先生講授詩文時,必先把內容吟誦一遍,再由學生循聲合誦。“風聲雨聲讀書聲,聲聲入耳”中的“讀書聲”,就是吟誦之聲。
清末民初的“新青年”大抵是最後一代讀過私塾的學子。從他們回憶私塾生涯的著述中,我們仍能一窺昔日塾生吟誦的熱鬧光景。劇作家齊如山憶述自己在村塾讀書的日子,十幾個小孩扯開嗓子,一喊就是一天。郁達夫說過,外國人形容中國人讀書和背書時“身體東搖西掃,搖動得像一個自鳴鐘的擺”。對他來說,讀書是件樂事,因為一整天坐在書桌前,唯一的運動就是吟誦時死勁搖擺身體和放大喉嚨高叫。趙元任回憶兒時唸書不照平常說話的聲音,而是打起腔來唸,唸的文體不同,調兒也不同。豐子愷也提過先生從不講解經文意義,只讓學生跟着他“唱”,其漫畫把兒時“誦讀鬥高聲”的情景描繪得十分生動。
為什麼古詩文要吟誦出聲?漢語是單音節語言,聲調起伏有致,像一個個鮮活的音符。古人作詩為文,往往不是一筆筆寫出來,而是一聲聲吟出來的。杜甫“新詩改罷自長吟”,賈島“二句三年得,一吟雙淚流”,陸游“鍛詩未就且長吟”,魯迅“吟罷低眉無寫處,月光如水照緇衣”,那是詩人墨客在一遍遍曼聲吟哦,推敲詩句。珠玉之作,非吟誦無以見其妙傳其神。俞平伯在《略談詩詞的欣賞》中指出:“當時之感慨托在聲音,今日憑藉吟哦背誦,同聲相應,還使感情再現。反復吟誦,則真意自見。”
一九零五年,清政府廢除科舉,私塾日漸式微。西學東漸,課程加入數學、體育、常識等科目,教育更趨全面。國文課本也不再局限於四書五經,加上白話文興起,吟誦逐漸淡出課堂,遭人遺忘。吟誦,曾經像呼吸一樣自然,是每個讀書人的基本功。一代又一代士子通過吟誦識文斷字,啓蒙開智。然而,不過短短數十年,逾千年傳統便瀕臨消失。朱自清在《論朗讀》中分析指,多數學生既不懂欣賞古文舊詩詞,又不能寫作文言,主因就是“不會吟也不屑吟”。
上世紀三四十年代,趙元任、夏丏尊、葉聖陶、朱光潛等學者開始整理和研究相關資料,為恢復吟誦大聲疾呼。然而,如果只知其事,不聞其聲,吟誦只能永遠留在故紙堆中,終將被歷史淘汰。踏入二十一世紀,曾讀過私塾或有家傳的老人逐漸故去,搶救吟誦調的錄音工作迫在眉睫。有些老人未及接受採訪,便已作古;有些只學過詩詞,不懂文賦吟誦。幸有學者排除萬難,組織團隊採錄、整理吟誦調式,並編製古詩文吟誦教材,培訓語文教師。在多方努力下,吟誦再度得到大眾關注。
粵語有九聲,較普通話保留更多中古語音,用來吟誦古詩文,更能體現其音韻之美。廣東吟誦雖名列“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”,但知者甚少。為挽救粵語吟誦,有人四出尋訪老先生,蒐集碩果僅存的吟誦調,並從碩學鴻儒的講學錄音中找出吟誦片段,為之記錄音譜;亦有人著書論述,並指導學生吟誦詩詞。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二十世紀香港粵語吟誦典藏網站,上載多位教授的吟誦錄音,彌足珍貴;又每年舉辦“露港秋唱”古典詩詞吟誦會,廣邀名家學者吟誦詞文作品。弦歌不輟,吟詠之聲仍在香江迴盪。
當代最負盛名的古詩詞學者葉嘉瑩大半生致力推廣吟誦,自言有兩個心願:“一個是把自己對於詩歌中之生命的體會,告訴下一代的年輕人,一個是把真正的詩歌吟誦傳給後世。”相信只要愈來愈多人了解、關注、感受吟誦的魅力,這位期頤老人的心願必能達成。